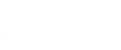本周推荐——《史记的读法》
中学阶段语文教材中选编了多篇《史记》中的文章,《鸿门宴》、《屈原贾生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等都是同学们耳熟能详的篇目。《史记》注释类的书籍很多,本周推荐台湾历史系教授杨照老师的《史记的读法》,希望有助于大家更好的理解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思想。
书名:史记的读法
作者:杨照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19
ISBN:978-7-5598-2060-0
索书号:K825/186
适读人群:老师、学生、学生家长等
豆瓣评分: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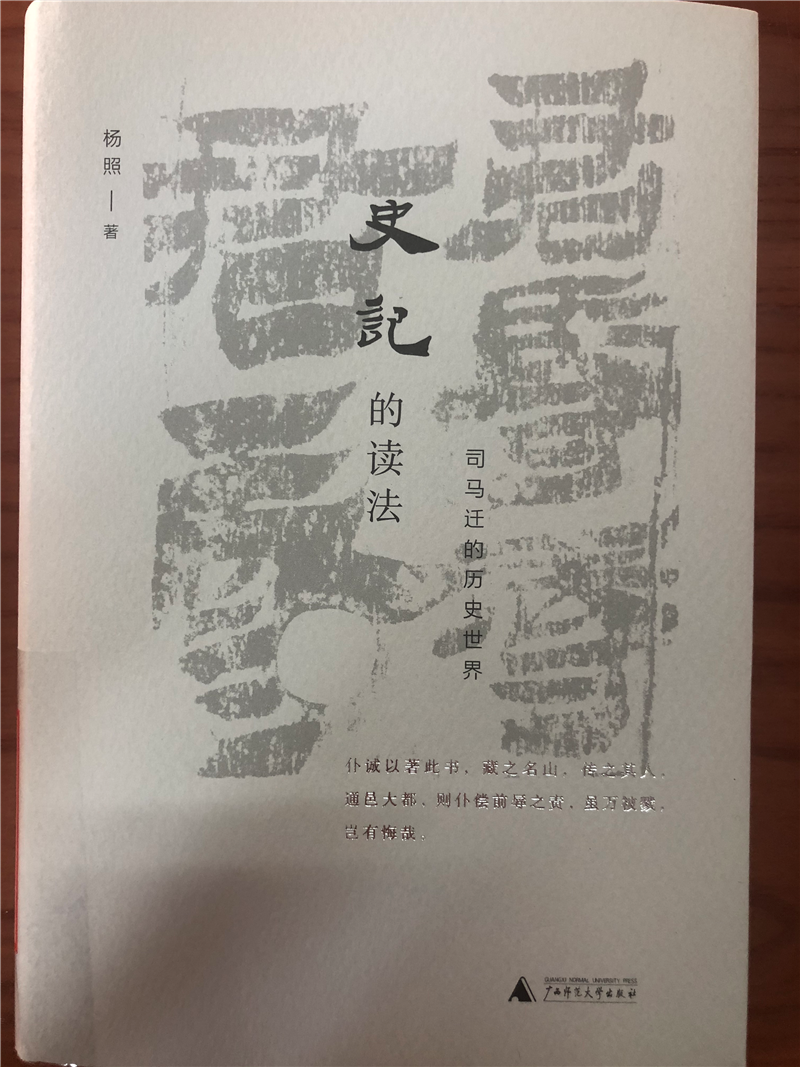
作者简介:
杨照,作家、文学评论家。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曾为哈佛大学史学博士候选人,师从杜维明教授,研究专长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社会人类学。最近十几年来,一直致力于各种东西方经典著作的解读,并担任“诚品讲堂”、“敏隆讲堂”长期经典课程讲师,“看理想”古代中国经典节目主讲人。
主要著作有:《史记的读法:司马迁的历史世界》《经典里的中国》《故事照亮未来》《想乐》《我想遇见你的人生》及现代经典细读系列等四十余种。

内容简介:
本书是看理想的口碑节目《古今:杨照史记百讲》精编而成。作者打乱《史记》原来的篇章次序,以“历史式读法”还原当时的社会背景,解释重大事件的因由,以“文学式读法”去接近司马迁的视角、态度与理念,把经典带入今天的时空。他从《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开始,解读司马迁的切身遭遇,进而从《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吕后本纪》等篇章分析汉代初期的历史,表现司马迁对汉初政治运作的锐利观察。在多重时间维度的观念中,《史记》中的“表”和“书”可以突显司马迁的突破性创意;而本纪和列传的布局谋篇中,也可以发现司马迁眼中谁才是值得载入史册的典范,哪些价值才是让他耗尽全部心神写完《史记》的动力所在。
相关评价:
如何从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的尺度去看待《史记》是一回事,如何就书论书地读《史记》则是另一回事。作者显然并没有把精力放在前一个维度之上丝毫,却在后一个维度之上做到了淋漓尽致。自疑古派以来,我们似乎太过于重视“求真”了,以至于忘了太史公的本意或许并不在此,“究际天人、通变古今”,把探察史料感知出来的史论凝结成一家之言展现出来,才是太史公之本意。
—— 寒鲲
史记,是人的事迹,上至帝王将相、诸子百家,下至刺客游侠、占卜医者,是一部最原初的中国人的心灵史,究天人之际,在顺应天道之外,燃烧个人的才华,担当应有的使命,找寻个人安身立命的根基。
—— 若尘
读此书才第一次理解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真正含义,作者将史记精华浓缩也正是以此为例来对这三句话进行解释。汉代的历史条件下,司马迁在著史过程中的遗漏和局限性我们都不能过分苛责,但其对历史的认知和态度却一直传承到了当代,特别是在信息收集、整理和检索水平都高度发达的今天,不论是著史还是读史,视角仅仅放在历史事件本身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从历史的表象中找出客观规律,通过历史认知现在,着眼未来。
—— kederer
相关报道:
杨照:历史普及等同于讲故事,这低估了大众的智慧
采写 | 徐悦东
在班固之后,正史的写作者为何没有真正传承下《史记》的写作构架及其背后的精神?司马迁撰写《史记》的背后,到底持有着何种精神?我们该如何进入《史记》的文本?在历史普及的过程当中,又存在着什么常见的误区?就这些问题,我们专访了作家杨照。
《史记》作为二十四史之首,其影响力和开创性是巨大的。不过,作家杨照却认为,在班固之后,正史的写作者并没有真正传承下《史记》的写作构架及其背后的史观和精神。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正史写作又丢失了《史记》中的哪些传统?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中,“成一家之言”为何会最被后来的正史写作者忽视?
我们要了解《史记》的写作构架,首先要理解司马迁复杂的心灵结构,这也是我们进入《史记》文本的一种有效方法。此外,杨照还提到了近几年流行的大历史著作,并甚至认为司马迁的《史记》早就在这么写历史了,而且他书写的方式更加吸引人。司马迁撰写《史记》的背后,到底持有着何种精神?我们该如何进入《史记》的文本?在历史普及的过程当中,又存在着什么常见的误区?讲历史故事就等同于普及历史?趁着杨照《史记的读法》新书出版之际,新京报记者与杨照探讨了这些问题,也聊了聊杨照的历史普及工作。

新京报:这本书的书名叫《史记的读法》。为什么你讲《史记》,会从司马迁写《史记》的视角出发来进入《史记》的文本?在读《史记》的时候,你提倡的“历史式的读法”和“文学式的读法”,和你以前讲经典的方式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杨照:司马迁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他处在一个特别的时代,有着特别的人生经历,更重要的是,他有着特别复杂的心灵结构。在阅读《史记》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真切地认识到司马迁写《史记》的原因,我们就没有办法确切地了解《史记》。这是我多年探究《史记》所得到的结论。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用这种方式来阅读《史记》,这是一种特别有收获的读法。
所谓“历史式的读法”,是指我们要了解司马迁和他处的时代,以及司马迁写《史记》的历史观。我们一定要去理解他写这本书的背景。相比之下,“文学式的读法”是容易的。我们一般读《史记》基本上用的就是 “文学式的读法”——我们喜欢读《史记》里精彩的故事,对司马迁笔下的人物有所认同。不过,因为司马迁的作者意识太强大了,所以在除了“历史式的读法”跟“文学式的读法”之外,我们还要对于司马迁的心灵和精神再多一点认知。
这种读法和我以前讲经典的方式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不过,读《史记》的方法比起其他经典会更复杂和吊诡。对于一些经典来说,我们基本上可以把该经典跟作者分离开来看待。可《史记》不同,我们越了解司马迁,就越能够挖掘出《史记》的精妙之处。

新京报:司马迁写《史记》基本以人物为中心。这种以人物为中心的写法似乎对中国古代的历史书写产生了很大影响。甚至到现在,很多人对历史的理解还是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杨照:这种现象是一种遗憾。这起源于大家对于司马迁的误会。纪传体是被纳入到中国正史的书写体例,而《史记》被放在正史第一的位置。这中间经历了很多波折。中国正史中的纪传体,其实和司马迁写的纪传体是不一样的。
二十四史里面的大部分史书,一定有本纪和列传。可是,司马迁不是这样架构他的《史记》的。《史记》里有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个部分,这五个部分构成了有机的整体。在这个意义上,司马迁之后的史家没真正把握司马迁写纪传体的精神,这是令人遗憾的。二十四史里许多正史并没有志书。《汉书》还继承了志书。志书是脱离人物的制度史。《史记》之所以有志书这种体例,是因为司马迁太了解历史上有太多东西不能用人物来解释。在司马迁所记录的时代里,有着许多种计算时间的方式,这时我们需要表,才能够厘清历史脉络。书和表在《史记》中的地位都是非常重要的。
![《史记(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汉]司马迁著,中华书局2013年8月版.png 《史记(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汉]司马迁著,中华书局2013年8月版.png](/cms/lib/CNBJ000005/Centricity/Domain/220/36656/《史记(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汉]司马迁著,中华书局2013年8月版-20191223164054349.png)
此外,司马迁笔下的本纪,并不是有着帝王将相的史观。对司马迁来说,本纪只是《史记》的一部分。他把本纪放到《史记》的最前面,不是因为本纪最重要,而是为了方便。司马迁用本纪来进行断代,并展开该时代的主要政治事件。这并不是替帝王立传的写法。
汉高祖的事迹被大量地记载在《高祖本纪》上。但是,如果我们要充分地认识并理解刘邦,看《高祖本纪》是不够的。我们至少还要看《项羽本纪》。其实,刘邦的许多事迹写在了《留侯世家》、《陈相国世家》和《淮阴侯列传》里。因此,《高祖本纪》并不是刘邦的传记。这是个误会。在《史记的读法》里面,我非常希望能纠正这个误会。
之所以有人会认为,以人物、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史观是来自于司马迁,这是因为我们用了一种割裂的方式去读《史记》。一般来说,我们读《史记》只读几篇本纪和列传,这并没尊重司马迁创作时搭建的架构,也没有理解司马迁背后的野心。司马迁不是为了歌颂帝王将相,恰好相反,他抒发的是官吏的抗议。《史记》的构架和背后的史观、心灵和精神,在班固之后都没有被传承下来。这才是我今天试图去还原司马迁的本相和《史记》完整内容的原因。
假如司马迁知道罗马帝国,他也会将罗马帝国写进《史记》
新京报:为什么司马迁的这种结构没有被后来的史书传承下来呢?
杨照:因为他的史学观念太过于超越了。他超越了他的时代,还超越我们一般的观念。一般人会把历史当作一种简单的事件罗列。但司马迁的野心,是要整理从他那个时代往前能够追索到的所有人类经验。假如司马迁知道西方有罗马帝国,他也会把罗马帝国写进《史记》的。
书写和整理过去人类经验才能“通古今之变”。司马迁不只有这么庞大的野心,还有可执行的方法,并产生了相应的书写架构。古往今来,很少有这种野心的历史学家。在21世纪,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些类似的野心,比如像《人类简史》。初看到《人类简史》时,我们会被吓一跳,作者怎么敢把完整的人类历史放进一本书里面呢?
但司马迁早就这样做了。而且,《史记》比《人类简史》的表现方式更具吸引力。因为司马迁清楚,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在整理人类经验时该用什么标准和逻辑来架构。这太超越了,因此没有被传承下来。

新京报:你在书里写到,司马迁写《史记》除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还要“成一家之言”,但不幸的是,“成一家之言”在中国后来整个史学里面反而成了最难理解的一件事,这该怎么理解?
杨照:到现在,在通俗的语境里,历史就是指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都这样认为,那么任何一个人来讲历史,讲法都是一样的,那历史学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因此,在历史研究和呈现中,“成一家之言”反而是最关键的。在宋代以后,这种意识反而进入到中国文人的文化里,因此文人爱写翻案文章。如果不能翻案,为何还要重讲历史?翻案是因为写作者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我们不可能改变秦始皇统一六国的事实,但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是秦始皇统一了六国。贾谊的《过秦论》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解释。后来,围绕着贾谊的《过秦论》,诞生出很多翻案文章和不同的意见,那才叫做历史。
“成一家之言”是历史学家最根本的职业自尊之一。可是后来,“成一家之言”在中国史学传统中,被隐没在集体性真理的底下了。正史的作者们失去了个人性。历史学家如果没有“成一家之言”的基本自尊,那历史学本身就会变成极度没有专业尊严和无聊的一件事。司马迁在两千年前写《史记》的时候,早就把“成一家之言”标榜得很明白。
新京报:像你刚才提到《人类简史》,这几年,大时空尺度的历史叙事似乎一下子流行起来。《人类简史》在世界范围内带红了“简史”系列,也让“大历史”进一步走进中国公众的视野。但有很多人也批评,这种大历史的世界观会过于简单,构建一个简单易懂的框架,读者就可以以最快的时间,把碎片化的知识整合起来,让有知识焦虑的读者读完之后缓解焦虑。你怎么看待这种大历史写作的流行?
杨照:大历史有很多不一样的写法。我自己比较反对的一种写法是,把人类历史发生过的事情,简化成多少件事,然后把这些事浓缩进一本书里。这是最糟糕的一种写作方法了,因为简化了之后,书里的内容就失去了我们之所以要了解历史根本原因——我们要去了解人的行为是受什么动机、心理和观念影响的,以及这些行为在历史上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当我们把历史事件全部简化之后,它们彼此之间的因果关系就很难进行解释了。这种大历史是不值得读的。
大历史还有其他写法。如果写作者能有一些不同的角度,比如以技术的改变作为主轴,去解释历史上这些事件背后的原因。这样就能在较小的篇幅里,书写人类的大历史。在威廉·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轴是围绕着一个问题而展开的——为什么从小亚细亚到爱琴海所产生的文化跟社会组织的原则,经过两三千年的变化和发展,最后笼罩了全世界?这是这本世界史的主题。这种写法的意义在于,让读者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人类历史的变化。当然,写大历史的作者内心是要谦卑的。因为他们也要知道,他们给大家提供的视角只是解释历史的其中一个角度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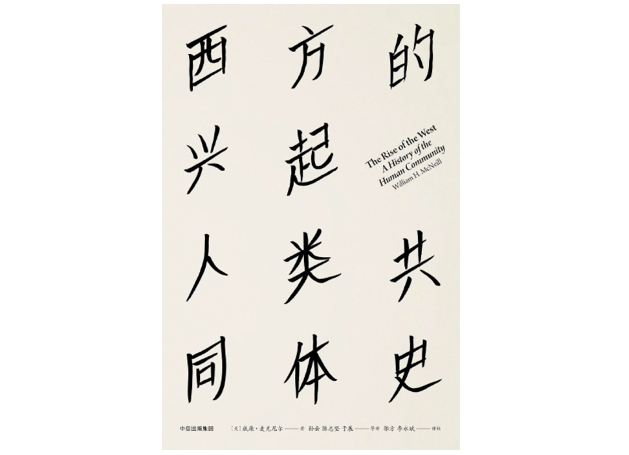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个“完整历史”,他的用意和写大历史的历史学家也不一样。他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以,他在选择呈现那段历史的时候,首先有他的标准。“天”是巨大的、集体的和外在的力量,是个人没有办法转移的。这不是司马迁要探索的或记载的。司马迁要记录的是人,他们如何运用个性和智慧,做了什么事。“通古今之变”意味着,司马迁从这些人的行为中整理、统纳出一个转折变化的模式。更重要的是,司马迁要“成一家之言”,这意味着司马迁的历史不是一个终极版本。而司马迁之所以选择记载和呈现那些历史的原因,都关乎人伦的阵痛。这来源于他儒家的价值观。
因此,《史记》除了书写的时间很长,其书写的人物也很广。我在《史记的读法》里特别选了《日者列传》。日者就是卜筮者。为什么卜筮者值得被写进《史记》里?司马迁认为,卜筮者在人类经验的传承上拥有特殊地位。此外,这背后还隐藏了司马迁的态度——当时的人常常以为主要的人才都在朝廷里,这是一种偏见。司马迁认为,其他领域还有很多重要的人才。比如,当司马迁在写《扁鹊仓公列传》的时候,他除了讲中国古代的医学史,也讲了许多在医学行业里面的特殊人才。司马迁用这种方法去呈现他的大历史,是独一无二的。
新京报:您在书的最后一节说,当我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就会对人类行为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从而触碰到普遍的人类经验,这才能以古鉴今,让历史对当下有所帮助。但是您在其他访谈里也提到,您反对用现代的眼光读经典、解读经典的时候,假如用一种迎合现代的解读,让经典“古为今用”,是对经典作品的浪费。这里面会不会有矛盾呢?
杨照:没有矛盾。我反对的“古为今用”是指,我们是把古人看成跟我们一样的人,然后用当下的标准、行为去想象古人。当我们觉得,古人跟我们一样,遇到某些事情会有这样的反应,所以我们做的是对的。这不过是我们在拿古人来消遣今人,这是“轻薄古人”。我们没有真正谦虚地去认识古人。
我们读经典基本出发点应该是,古人是跟我们不一样的。这样的话,我们才会刻意找出古人在特殊的时代情境下,所做的事情跟我们的不同。若我们用这种求异的方法来看经典和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自己也受到时代和眼光的局限。比如说,我们看西乡隆盛在日本历史的情境当中,他面临的选择有许多种,但是他囿于时代的局限,他是看不到那么多种可能性的。这时候,我们再考虑这些可能性中,哪些是好的,我们这样才能长智慧。这是我赞成的“以古鉴今”,而不是把古人挪过来当隔壁老王的“古为今用”。古人绝对不是我们看一眼就知道他们过着什么生活的隔壁老王。这是我们对古人和经典都应该要有的基本尊重。
新京报:你曾说你看到中国历史的学术研究与社会常识的高度落差,就产生了为大众普及的使命感。你写普及历史的书籍,也做过“诚品讲堂”、“敏隆讲堂”的长期“经典课程”讲师,也在电台主持广播节目,也曾经做过电视节目,你觉得在这二三十年历史普及工作中,在大陆或者在台湾,在知识普及的环境上,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你有什么观察吗?
杨照:我的观察是大家都太爱讲故事了,而且还越来越爱讲故事。历史普及者都认为,给大众普及历史就等于讲故事。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他们低估了大众的智慧。好像只有给大众讲故事,大众才能听得进去。但历史不可能都是故事。故事只能够传递非常狭窄的历史经验。这使得大众以为,历史就等于故事,评断历史只看故事好不好听。其实,大众听再多故事也不能从历史里学到真正的智慧。
另外,在把历史化约为故事的过程当中,大家失去了把复杂的理论和与因果解释有关的历史解释,用一种容易理解的方式讲给更多人听的重要能力。这种能力是需要积累、培养和锻炼的。
因此,我一直认为,这段时间的历史普及的发展,反而更难生产出我希望的历史普及方式——用简单、清楚的话普及历史,但这段历史仍然是原汁原味的。直到现在,我们在学术上面已经取得的一些成果,和学术界普遍承认的一些历史解释,与民间的社会常识还是存在着高度落差。我真的很希望大家不要再那么爱听故事。我们还可以从心理学、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的角度去解释和分析历史人物的行为。因为历史更重要的是观念和思想,而这些东西都不可能简单地用故事呈现。普及历史就像搭桥,我们要搭一座桥,把桥那边学术富矿里挖出来的漂亮石头,运到桥的那边去。我希望有更多人一起来做这个事情。

新京报:刚刚你说到大家爱听故事,你觉得这会不会跟媒介的原因有关?新兴媒介的出现会对知识普及的工作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杨照:媒介变化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让历史戏剧化。我们一直都有这样的误会,大众可以通过看电视剧了解历史。其实这是不对的,用影视来呈现历史,这本身就是非常局限性的,因为影视这种媒介很容易把历史戏剧化。影视媒介的普及也反过来让许多历史普及者自我设限,只认为大众只爱看故事,这其实是在偷懒。我们怎么把故事之外的历史知识,解释给更多人听,这才是历史普及者面临的大问题。
新京报:你在以前的访谈中说过,像《百家讲坛》这样的知识传播方式和受众的假定是跟你有差距的,你假定自己面对的是一种“中间读者”。这种有一定基础的“中间读者”的数量也许是比较少的。你为什么选择“中间读者”?你会担心市场吗?
杨照:现在已经有太多人在照顾在学术界里的尖端读者了,我也插不上手。而我完全不会写真正大众要看得懂的通俗读物。对学术界来说,我是“不为”,而对真正的大众来说,我是“不能”。因此,我不是主动去选择“中间读者”。
其实我认为,《百家讲坛》的老师们都比我厉害,他们能把历史和经典讲得这么生动精彩。我没这本事。我可以做到的是,和有一点基础又想要更深入学习的读者沟通。既然这是我这样选择,我的市场就是这些“中间读者”,这叫做“求仁得仁”,我也没什么好担心市场的。

我以前说过,一个社会是什么样的,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这个社会有多少“中间读者”。“中间读者”的数量一定不会多。但这个社会有3%或者18%的“中间读者”的差别很大的。我知道“中间读者”的市场可能只有8%,我就尽力服务这8%的市场。若靠大家的努力,我们把读者比例从8%扩大到8.5%,那也是功德无量了。
新京报:有人说知识付费是一种制造和利用知识焦虑的商业模式,这和以前的传统的知识普及形式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你是怎么看待知识付费的商业模式?
杨照:所谓知识付费也不是铁板一块。知识付费有很多种不同的形式。最流行的知识付费是让你付钱听课,然后你就能学到有用的知识。这是一种功利的方式。而像“看理想”的商业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在上面讲的这些知识都没有实用价值的。大家要听只有一个理由,就是想让自己变得更丰富。这个节目更深刻的作用就是,本来大家以为人只能这样活着,但在听过这个节目之后,听众也许会觉得,自己原来以前过的生活太狭窄、空虚和贫乏了。
这是不是在利用知识焦虑?这其实不是知识焦虑。我觉得这是更大的“恐吓”,我们的商业模式更“可恶”,因为它在输出一种“生命贫乏感”。我们在刺激听众,问他们活得还好吗?活得丰富、满足吗?我们该怎么活着?我们会不会太空虚了?假如我们觉得太空虚的话,就来付钱听我们这节目。这跟我们一般讲的知识焦虑是不太一样的,也是不同层级的东西。但这种层级的东西一定要有人去做。而用这种方式,卖诉诸生命贫乏的需求的课程,本来就不可能有很庞大的市场。我对这种商业模式跟我对“中间读者”的态度是一样的。如果这东西的市场越大,这个社会就必然会变得好得多。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近年来中国的“经典热”、“国学热”?
杨照:我希望近年来的“国学热”和“经典热”是真的。真的“国学热”是指,我们在整理中国传统之后,这些传统要跟我们的生命发生关系。比如说,两千多年前的《史记》,因为有了“国学热”,《史记》和我们的生命发生了联系。我很希望这样的热潮能笼罩我们,让我们变得不一样。
但是,我担心这种热潮不是真的,这意味着当我们讲国学的时候,我们不是真要去看《史记》、《庄子》或读韩愈、柳宗元的作品。我们不是真要把唐诗,从它的格律到内在精神都彻底跟自己结合起来。我们太容易把老子、庄子、佛家放在口头,动不动就说这是佛家智慧的体现,但我们从来不认真地去看佛教是怎么变成汉传佛教的。汉传佛教是很庞大的传统,与天竺的佛教大为不同。国学就是要去仔细分辨佛学进入到中国传统后是如何变化的。若这些东西我们都不去做,就把佛和禅放在口头上,这是假的“国学热”。说实话,我现在没有真感觉到“经典热”和“国学热”热起来了。我只是感觉到了这种气氛,但我真的很希望这种气氛可以落实下来,更重要的是让从个人阅读理解到连接我们生命的这部分变成真正的潮流。我对此还是抱有期待的。
参考文献:
[1] 杨照.史记的读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2] 杨照:历史普及等同于讲故事,这低估了大众的智慧[UL] .http://news.sina.com.cn/c/2019-11-13/doc-iihnzhfy8945326.shtml